第9章
我衝她吐舌頭:「他的就是我的。」額,鬥嘴鬥快了,我心虛地偷瞥一眼某人,還好,他面色如常,沒拆臺。
「栀栀......他們是誰啊?」顧景然醒了,揉著眼睛,一臉茫然,他不認得臻觀了,把畫中發生的事都忘了。
我敷衍介紹,和尚,道姑,萍水相逢。
顧景然拉著我就要走。
「該回去了,找你一天了。」
哦,該回去了,該跟他們分道揚鑣了。
失落感忽地罩落下來,嘴裡的糖不甜了。
我望向臻觀,揉著袖子,低聲告別:「那我......走了。」
他站在燈火闌珊處,半張臉籠在黑暗裡,略顯蒼白的唇微動。
「嗯,一路平安。」沒有挽留。
微風乍起,黑暗中的雪色僧服掀起微瀾。
我收回目光,不敢再多看一眼,轉過身離開。
長街盡頭,我還是忍不住回過頭看,白衣僧人已經消失在夜色中了。
「顧景然,那賣糖葫蘆的還在嗎?」喉嚨莫名發苦,需要吃糖。
「......你都幾歲了,還吃......」
我踹他一腳:「滾去給我買,不然回去我找皇兄告你黑狀。」
Advertisement
15
在佛陀城最後一夜,睡不著,窗外忽然傳來窸窣的聲音,像無數人擠在一起低語,嘆息,呵氣,一層雞皮疙瘩被激起。
我提起燭臺挪到窗邊,撥開一角環顧,聲音消失了,一片寂靜,四周黑漆漆,什麼也沒有,聽錯了吧?剛松一口氣,準備關窗,手背突然一燙,一滴血濺開。心中劇烈一跳,抬頭看,半空中懸著一個血月,像融化了的火燭,大滴大滴往下淌血,手一顫,燭臺跌落。
低頭一看,地上躺著數十個支離破碎的人,上百人圍著他們,啃骨噬肉,狼吞虎咽......我死死捂住嘴。
空中紅月秾豔,地上血流成河。
風打窗而過,呼地發出砰聲,他們同時抬起頭來,齊齊望向我,對著我森森笑起來,滿口朱紅鮮血。
「來啊,一起吃人啊。」
我煞白了臉,踉跄往後退。
「咚,咚,咚。」
客棧樓下驟然響起劇烈敲門聲,不是一個人敲,是無數人在敲。
「哐哐哐。」幾乎要將門砸了。
有人打著呵欠應聲:「來了來了,催命呢。」
我醒過神,衝出去,在走廊上急聲喊:「別開門,把門堵上。」
小二被我唬住。
「栀栀,怎麼了?」顧景然醒了,來不及多說,我讓他領護衛下樓,堵住門窗。
店內房間陸續亮起燈,有人罵罵咧咧:「吵什麼吵,半夜三更的。」
我撿了走廊角落備用的銅鑼敲喊:「殺人了,殺人了。」
一時間,小兒啼哭,婦人惶然,男人踹門......
眾人被驚醒,驚慌失措衝到樓下。
外面的敲砸聲愈發劇烈,所有人面色鐵青,死死堵住門窗。
「究竟怎麼回事?」「外面有人在吃人。」
所有人臉色瞬間刷白,有人唇抖得像落葉,喃喃道:「又來了。」
「什麼又來了?」
「二十一年前,少城主出生那晚,天上升起血月,城中許多人突然發狂,人吃人......」
我心中一跳,少城主?臻觀。
那人發抖顫聲:「那晚被血月濺到血的人,都發了狂,到處咬人,吃人,死了好多人......」
手背上那滴血忽然發燙,我捂住手,驚恐地後退。
「那些發狂的人呢?最後他們怎麼了?」我無力地問。
「死了,都死了,他們咬人,吃人,被他們咬到的人也開始吃人,就跟瘟疫一樣......後來來了一群和尚,他們說隻能把這些人燒死,不然他們會繼續咬人,這場吃人的瘟疫就會無休無止。」
然後呢?
「老城主下令將他們燒死了......」
我手腳發冷。
門外的敲砸聲忽然消失。
所有人屏氣凝神聽著,沒有任何動靜。
過了良久。
「他們好像走了?沒有聲音了。」
有個人悄悄推開窗,往外看。
「沒人了。」他回過頭來, 明顯松了口氣。
「背後有人!」一陣尖叫。
無數雙纏滿紅色新娘花的手從窗口插進來。
血肉橫飛,有人失禁,癱軟在地。
「啊!」少婦死死捂住少兒的眼。
眨眼,一雙帶血新鮮眼珠滾落在地,牆上濺滿腥臭生血,空中肉塊橫飛,窗外無數瘋人同黑色蝙蝠破窗而入。
「走,快走......」顧景然拉著我往後退,可走哪去,窮途末路。
這是一場單方面的屠戮。
無數驚恐尖叫聲交織在一起,刺破寧靜夜色。
前面的護衛一茬茬倒下,成了牆上的朱血,地上的爛肉。
隻剩下顧景然站在我面前。
耳邊不斷有聲音催促我。
「餓了吧,渴了吧,小殿下,吃肉啊,喝血啊。」
餓了,渴了,我直直盯著前方的顧景然,手搭上他的肩。
忽地,眼前閃過無數道金光。
「萬神朝禮,役使雷霆,破。」
正在吃人的瘋人被定住,一動不動。
耳畔響起那道沉穩微醇的低喚聲:「小殿下。」
我茫然地眨了眨眼,轉過身,下一瞬被按入一個泛著淡淡檀香的懷抱。
「小殿下,沒事了。」他輕輕摸我的頭。
我眼眶漸漸紅起來,嗚咽著:「臻觀......」想伸手抱緊他,可猛地想起來剛才發生的事,如果不是他來了,我想幹什麼?
我惶惶收回手,拽下袖子掩住自己的手。
被濺到血的人會開始發狂,他們就像瘟疫,我是瘟疫......
我害怕,尤其害怕被他發現。
「小殿下,不怕了。」他一遍遍拍我的背,音色沉穩,撫平發亂的心。
死裡逃生的人圍在四周,驚詫地看著我們,他視若無睹。
有人推門陸續走了進來,一些城衛,還有,阿依姑娘。
「臻觀哥哥,他們很快就會醒的。」她嬌糯的聲音響起,令我清醒。
我慌張地推開臻觀,後退幾步。
他將我拉回身旁,神色微肅:「跟緊我。」
「立即封鎖朱雀街。」他以少城主的身份發號施令。
混亂的血月夜暫時平息。
16
我們跟著臻觀回到城主堡。
吃飯時,見到了老城主和老夫人,他們很熱情地招呼我們,不過,親疏有別。
「觀兒,給阿依夾點菜。」老夫人吩咐臻觀。
阿依微紅了臉,有些羞澀。
我掃了一眼臻觀,他微微探身,沉默著,給阿依姑娘添了筷子菜。
哼,過了除夕,他一還俗,他們就......我戳了戳碗裡的飯。
「謝謝臻觀哥哥。」她叫哥哥叫得很甜。
我攥緊筷子,低頭蔫蔫夾了幾顆飯粒,米飯一點都不香,我踹鄰座的顧景然,他一臉疑惑,我無聲指示他:「給我夾點肉。」
他咬著筷子,歪著頭,沒看懂,人頭豬腦,我忍不住又踹他一腳。
眼前忽然橫過來那雙白淨纖長的手。
瞬間,我的飯碗上壘起小山,抬頭撞進那雙沉靜無瀾的眼眸。
他面不改色看著我:「多吃點。」誰要他夾的,不稀罕。
「臻觀師父太熱情了,我吃不了這麼多,顧景然,你幫我吃一些吧。」
我把他夾的都撥給了顧景然,不經意瞥了他一眼,他清雋眉間隱約透著一抹灰暗。
回房間沒多久,有人敲門,推開。
「臻觀師父,又怎……」我不打算請他進屋,但是目光下移,瞥見他端著的那碟葡萄,我沒骨氣地把話咽回去,「請進。」
他坐在一旁安靜地剝葡萄皮,垂著眼眸,神色認真。
我百無聊賴擺弄桌上的茶杯,出於禮節,他不說走,我又不好趕他走。
他剝了一顆遞到我唇邊,面色如常,聲線溫和:「吃吧。」
我看著他沉靜白玉顏,受蠱般,怔怔張嘴含住,不小心碰到一點微涼,一看,他的指尖上勾了一抹水色,我急忙解釋: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臉不爭氣地燒起來。
他斂眸不語,聚精會神盯著指尖,微微蹙眉,眉間朱砂有些發紅。
嫌髒?
我抽出手絹遞給他:「喏,你擦一下吧。」
他沒接,卻盯著我,將指尖抵在唇邊......
他唇上泛起旖旎水澤,眸色逐漸深暗。
我被他看得心裡發慌,站起來,支吾著:「那個,我……我不吃了。臻觀師父,你要不先走吧,我想休息了。」
他站了起來,比我高出許多,站在面前,很有壓迫感。
「沒吃幹淨。」他不輕不重說了聲。
我疑惑地望向他,又見他眉間朱砂鮮豔。
我拿起手帕要擦,卻聽見他微啞的嗓音:「別浪費。」
什麼別浪費?
下一瞬,他捏著我下颌,柔軟冰涼的唇壓上來。
心跳如鼓擂,我渾渾噩噩抓著他的袖子。
「為什麼分給他吃?」他將我揉進懷裡,嗓音喑啞。
我有點懵。
「顧景然。」他語氣不善。
啊,當然是因為鬧脾氣啊,可怎麼說出口,我沒答他。
他微眯起眼,凝視著我,見我沉默,懲罰似的,吮得更用力。
「......別了......唔。」雙腿顫抖,差點站不住。
沒有畫,沒有檀香的驅使。
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,我昏昏地回應。
正對面是梳妝鏡,混亂中瞥過去,恍惚看見,身上的男人,是一副披紅白骨,我揉了揉眼,再看。
一盆冷水兜頭潑下來,我驟然用力掐住他的手臂,他悶哼一聲,抬起微紅的眼望我,聲音迷離:「小殿下......」眉間朱砂紅似鮮血。
「你是誰?」我驚懼問。
他不是臻觀,是鬼。
他隨著我的目光望向身後,白玉顏上浮現一抹異樣神色。
「我是臻觀。」他收回視線,定定望著我,眸光浮動。
我怔怔搖頭:「你不是,你是鬼。」
他眸光瞬間沉暗,那張泛著水澤的唇有些蒼白:「小殿下......」
熱門推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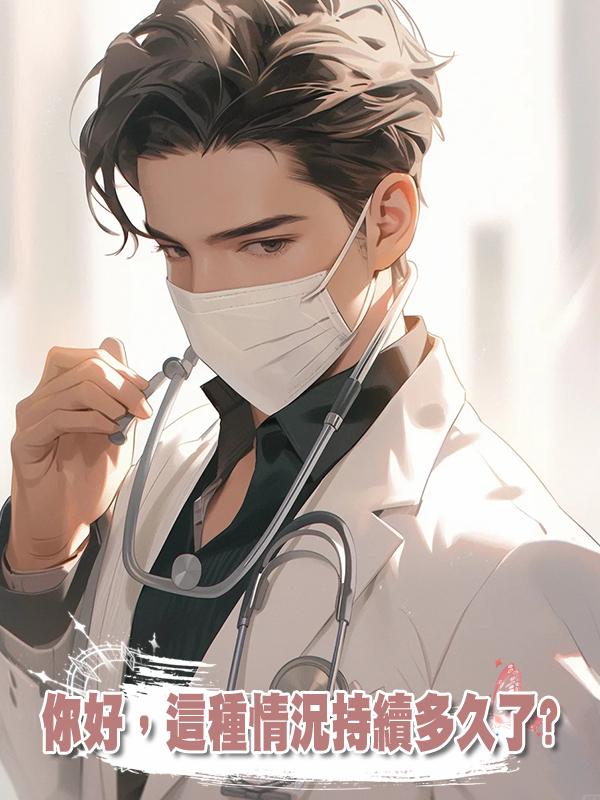
你好,這種情況持續多久了?
"程式設計師陶知越穿成了一篇狗血總裁文裡的炮灰,他是書中導致主角攻霍燃殘疾又心碎的初戀,最後被主角夫夫報復致死,格外悽慘。 陶知越毫不猶豫,當場跑路。"

蓉妃她權傾朝野
皇上跟我說:「蓉妃,朕屬意立你為後,但為了朝政穩固, 繼後不可育有子嗣,你可願意?」我沉默半晌,最終託著七 個月大的肚子,麻木跪下,叩首:「臣妾,願、意。」

他超愛的
"看見哥哥被男人壓在角落強吻。 我震驚但偷拍。 誰知哥哥不願為愛做0,他逃他追,他插翅難飛。 後來那個男人用錢羞辱我,買哥哥的行蹤。 我不為所動。 他告訴我卡裡有五千萬,我直接抱大腿:「嫂子!你就是我親嫂子!」 可我美滋滋逛街時,卻接到哥哥的電話。 氣息不穩,咬牙切齒… 我和哥哥出生在同一天。 生日宴切蛋糕時,我去找哥哥。 經過一處陰暗處,突兀地聽到幾聲嗚咽。 似貓叫。"

愛你縱使繁華一場
"五年婚姻,末笙都沒讓厲御南愛上她,得知自 己患上絕症,她隻乞求十個月。“十個月後, "

柳丁味阿鴨
高考過後,我和閨蜜的生活都翻天覆地。閨蜜的爸告訴她,其實她們家是億萬富翁,她想去哪裡讀書就直接在當地買套 房。

一場失敗的救贖
"穿進一本青梅竹馬BE的小說。 女主選擇了天降男主,甚至不惜與竹馬決裂。 隻有他被困在了年少瘋狂滋生的愛意中,求而不得。 小說生出了意識,讓我來救贖他。 於是我從十七歲到二十七歲都陪在他身邊,整整十年。 在他二十八歲生日這天,我滿心歡喜地等著他 但,女主重生了。 當他一整晚杳無音訊時,我終於明白。 大家都希望小說裡的深情男二能另覓良人。 卻沒有想過,他除了女主,誰都不要。 所以,我該走了。"